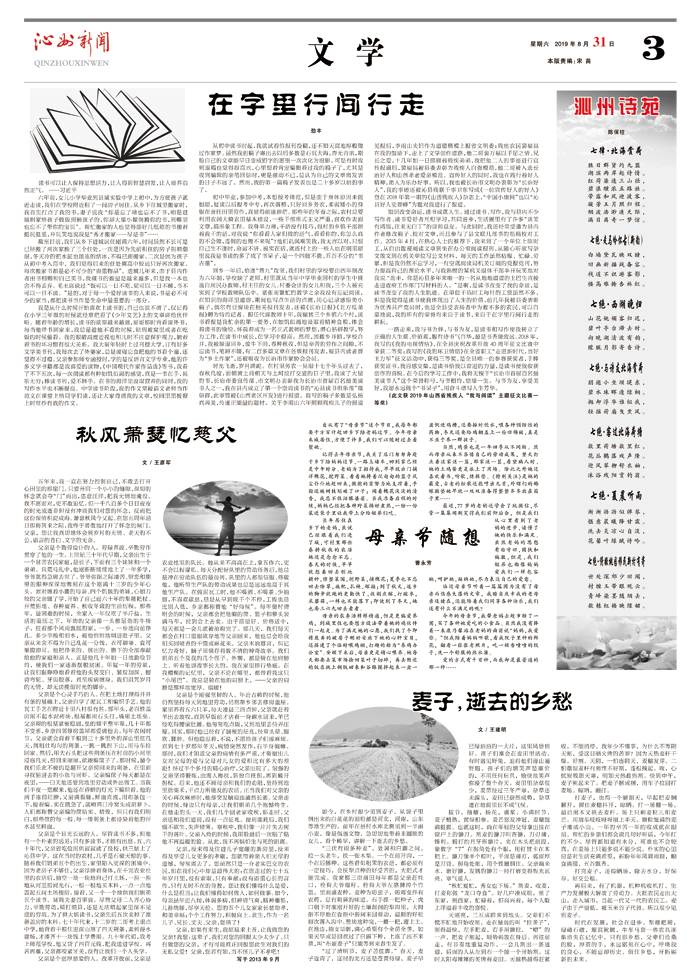如今,在乡村很少见到麦子。从袋子里倒出来的白花花的面粉都是河北,河南,山东等地生产的。前年在景村水库北侧见到一半亩小麦,像是偶遇文物,急切切地带着未圆锁的女儿,看个稀罕,讲解一下逝去的乡愁。
“三伏有雨多种麦”,处暑和白露之间,拉一头老牛,扶一张木犁。一个在前开沟,一个在后播种。这些看似粗笨的农活,都必须有一定技巧,会扶犁点种的好受苦的,大把式才能完成。我家那三亩薄田每年都是父亲赶牲口,栓狗大爷溜籽。栓狗大爷左胳膊挎个竹篮,里面盛麦种,麦种为防虫子,防霉变拌有农药,总有刺鼻的味道。右手抓一把种子,虎口朝下对准刚开好的土壤湿润的犁沟里,大拇指不停地在食指中指间来回滑动,温顺的籽粒顺次落入沟中。整块地种完,一耱一耙,覆上土。在地边,抽支旱烟,满心希望有个全苗全垄。如果天旱或是回茬过了白露下种,上冻了出不来苗,叫“布蛋麦子”只能等到来春生发了。
“过了清明节,麦子苫住脚。”春天,麦子返青了,这时的北方还是苍黄待绿,麦子早已绿油油的一大片,这里风景独好。孩子们准会在麦田里活动,有时遇见野兔,追得他们漫山遍野跑。孩子们的嬉笑声是廉价的,不用任何玩具,愉快地笑声弥漫了整个春天。麦田里杂草很少,麦苗经过三冬严寒,杂草还未露头,麦田已蔚然成势,杂草遮在地荫里长不成气候。
拔节,抽穗,扬花,灌浆。小满时节,麦子蜡熟,黄绿相参。麦芒怒发冲冠,麦穗饱满挺拔。也就这时,尚在年轻的父母拿出挂在窗户上的镰刀。割麦的镰刀叫杏镰,刀刃薄,锋利。锻打的月牙形镰片,夹在木头把前段,象数字“7”在拐角处有个眼,用钉贯卡在木把上。镰刀像半个粽叶,平面是薄刃,弧面厚是刀背。拐角处细,用个铁圈掴住。父亲端来水,磨好镰,发锈的镰刀一经打磨变得锃光瓦亮,寒气逼人。
“秋忙夏忙,秀女也下场。”割麦,收麦,打麦称做“龙口夺食”。好几户凑成组,割了东家,割西家,忙碌着,但高兴着,每个人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

天刚亮,三五成群来到地头。父辈们不慌不忙地开始收割。走在最前的叫“拉垄子”,割得最快,左手把麦,右手用镰拉,“噌”的一声,把麦子割起,顺势码放在身后。再往前走,有节奏地重复动作。一会儿割出一条通道,后面的人从左到右一个接一个开始割。这时太阳毒辣辣的炙烤着麦田。天越热越得赶紧收,不能消停。我年少不懂事,为什么不等阴天割,受这日晒火烤的苦罪?因为天热麦秆干燥,好割。天阴,一怕连阴天,麦穗发芽。二怕潮湿麦秆有韧性不好割,连根拽起。唉,心忧炭贱怨天寒,明知天热趁热割。快到中午,麦子割起来了。把麦子捆成捆,用车子拉回打麦场。晾晒,翻打。
打麦子,也得一个晴朗天,早起把麦捆解开,握住麦穗抖开,晾晒。打一场翻一场。最后用木叉挑去麦秆。场上只剩麦粒儿和麦芒。用扇车吱吱呀呀扇上半天。颗粒饱满的麦子堆成小山。一年的辛苦一年的收成就在眼前。帮忙的乡亲们都会说几句好听话,今年打的不少。尽管都知道有水分,可谁也不会较真,在麦场上只能多说不能少说。朴实的心里总是对生活充满希望,祈盼年年风调雨顺,粮食满囤,五谷飘香。
打完麦子,还得晒场,除去水分,好保存,好交公粮。
再后来,有了机器,机种机收机打。生产力发展极大解放了劳动力。大批农民走出大山,走入城市,当起一代又一代的农民工。麦子由于产量低,被玉米谷子代替。所以很少见到麦子。
时代在发展,社会在进步。犁耧耙耢,碌碡石礅,簸萁锹镢,牛车马套一些农具逐渐消失在记忆中。只有那乡愁,父辈们沧桑的脸,厚茧的手,永远铭刻在心中,呼唤我的良心,不能忘却历史。留住乡愁,开拓崭新的未来。